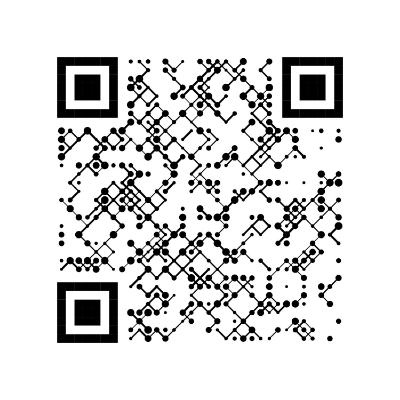《君与彼女与彼女之恋 》 关于其的精神分析讨论。
一.前言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大家也听说过这部作品作为十二神器的名声了,当然更多的是作为ddlc的前辈之作被拿出来进行比较的,因为都有很强的meta要素,当然我只是想讲一下我本来还计划要写一个关于现实与虚拟的尼采式的哲学讨论的这个事,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写了,就这样吧。


【剧透警告】
二.作为理想客体的超我
我们先来说说心一这个角色,他是理想自我的隐喻:他总是被爱着,被陪伴着即便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问题总是能够被包容和解决的,我们当然会移情于他,因为我们想要成为他因为他是理想的自我的欲望对象。
我们这时来说说美雪这个角色,他是内在客体与自我理想的象征她在社会层面上的评价是完美的也必须是完美的,她不会嫌弃你的出身,嘲笑你的无能,而是会稳定的和你呆在一起,但她有一个限制一个只属于想象界的限制:她与你绑定,她只服务与主体本身,她只是用来显示主体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她在班级中很受欢迎当然这种受欢迎是建立在一种表演上,而她消去这种伪装的方式是和心一建立联系,她作为一个客体的命运在葵将美雪与心一绑定时就已经注定了。
当我们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天台当心一第一次遇到葵,葵莫名奇妙的要和心一啪啪啪,这时美雪突然闯入阻止了主角与葵发生性关系,这个超我的隐喻不言而喻,超我阻止“我”进行超越道德与伦理的行动,她专断独行,独裁的阻止正常的性关系。
而在这里葵代表着自动运行的能指链,也代表着本我:她被社会与人群排斥在社会层面上她显得格格不入,她在第一周目中如同麦高芬一般,当真正运行故事的主体被揭示她必须消失。我们对葵的欲望虽以爱为名,但这种爱是癔症性的,而癔症创造的这种可见外部与不可见内部的对立则是无根据的,与此同时女性这一内在本质也等同于“创伤性”。葵吸引我们的,实际上不过是她的外在创伤。
我们同样可以在后来的问题中看到超我的隐喻,在第二周目当我们终于在顺应超我的原则下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真正的目的:“超越快乐原则”,我们终于追赶上了我们的痛苦。超我(美雪)通过旁敲侧击阻止我们靠近这注定毁灭的结局(和葵在一起),但最终我们跨过了这个界限,我们接受了这种痛苦仿佛痛苦本身就是一种欢乐,是为了达成某种欢乐必要的牺牲。但当我们一但突破了她,她便用极其严厉的手段:用她的菲勒斯毁灭了这个想象性的主体。她这种阻止也仿佛某种诱惑,如果没有这种界限我们并不知道打破这个界限,但现在它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仿佛等待我们打破它。

三.欲望对象a(最为重要的核心)
美雪和葵到底谁在这场欲望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哪?
我们在这里要先讲一个关与宙克西斯和帕拉西阿斯的绘画比赛的故事:宙克西斯与帕拉西阿斯比赛绘画,宙克西阿斯画了一个男孩举着葡萄,他的作品逼真至极,以至招来飞鸟啄食画中的葡萄。而宙克西斯并不满意,因为画上的男孩举起葡萄没有逼真到足以吓跑鸟儿。但帕拉西阿斯更胜一筹,他在墙上画了一块画布帘,这布帘如此逼真,以至于宙克西斯转生想要掀开它去看看里面到底画了什么。拉康讲问题不在于逼真性本身,而是在于凝视对视界驱力的构建,眼睛被欺骗不是因为逼真,而是因为主体满足于欺骗,欲望战胜了眼睛,让他忽视凝视本身而去猜想凝视后面的东西。
齐泽克曾说女性的独特是我们喜欢她的重要原因之一,而205891132094649分之一的曾根美雪也满足了这个主体要求的特殊性,但是问题不在于逼真性本身,就像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写的那样:“狐狸说: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世界里独一无二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你的世界里的唯一了。”就像这样当我们欲望葵或美雪时她就已经变得不同,她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象征她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即便是再平凡的事物也变得崇高了。
葵作为对象a而被欲望时,她是主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的存在,通过主体的不可能的欲望使她崇高化。正是主体的欲望的不可能,把主体送到了无限远的一个点,主体在哪里得以遭遇到实在界的面庞,对实在界的瞬间的凝视让主体陷入了盲目,主体被实在界之火灼烧了。
究竟是什么让二周目的那一刻有如此残忍痛苦的效力哪?
那便是上面讲到的实在界的应答,我们永远达不到欲望中的葵,但主体虽然与不可能之物总是失之交臂,但是它们毕竟要在某个地方交会,就像阿喀琉斯与乌龟的赛跑,不是阿喀琉斯跑得太快,就是乌龟爬得太慢,反正两者始终无法照面,只是在一瞬间擦肩而过,但终归还是有擦肩的时刻。而正是这个时刻,正是主体与对象a擦而过的这个相遇,让主体的观看以及主体因想象的凝视好不容易确立的象征权威顷刻间化为乌有,主体自以为稳固的想象秩序实际只是一个彻底的匮乏的补充,此时此刻,焦虑油然而生。
就像是再二周目,当作为主体的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是葵欲望的对象,她还有别的欲望的对象,即便她告诉我们这是她必然的使命(指NTR)我们也再也无法得到她,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性是爱的基本需求。倘若性不纯洁,那么爱也是不纯洁的了。
我们发现自己永远不能成为那个大他者欲望的欲望时,我们发现了自身的匮乏。这也是人类的 悲剧我们终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主体最终只能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叹:“我所得到的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们为了维系其与不可能之物之间的距离,拼命用想象性弥补我们的残缺用替代性的对象来置换真正的欲望对象的原因时,当我们拼尽全力接受她对我们的欺骗时,在这所有的替代以及由此而来的满足中,总是有某个东西从主体那里滑脱,每一次的替代和满足最终总是把主体引向根本性的匮乏,每一次重复总是把主体引向错失的相遇,我们与实在界相会了。
我们对不可能之物的追逐诱导主体成为了一个欲望的主体,一个欲望透过看来弥合他者缺口而最终是要被那道无法穿透的凝视之点撕成碎片的主体,如果说想象的凝视可以暂时地让主体在幻象的支撑中获得存在的意义,那么来自不可能之物的凝视就只会使主体再次去面对存在的挫败,匆匆踏上赴约之路,不过那是死神的最后的邀约。
至此,葵短暂的生命成为了永恒。正如普鲁斯特所说:“当一个人不能拥有时,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

观众们散场了 ,再见了世界 还会再见的吧,只有唯一的恋人,等候着你的到来 所以请务必来吧,呼唤着 神的声音,无法忘却的回忆 带上它们一起前行 ,无论到哪里一定会再见面的哦,就如星辰围绕着般的旋转木马。
四.永恒轮回
在这里游戏设计者利用巧妙的设计使主体进入了这个重复中,在游戏的最后:
和葵一起拨号的我——,只是注视着这一切,这是世界的夹缝,跳出游戏世界后,我们将前往不同的地方,葵是去神明大人身边,我是去现实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葵不会出现——,选项也不会出现,葵将变成强悍的刺客,拥有少女外表的魔导书,握着毛瑟手枪的天使,失忆的自动人偶,保护世界的天才魔女,女子乐队的贝斯手。我们只有不断的在其他的游戏中寻找这个原型。
这个机制我知道大家都看得出来了。在这里我们只有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不断的寻找这个不可能的原型,这个象征性葵的原型,当然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这就是游戏设计这所要做的,让主体明白他对享乐的追求已经得到满足,他已经到达了圣兆(sinthome)。
就如同齐泽克所讲的那个故事,一对兄弟抢劫银行,哥哥让弟弟在警察来的时候吹口哨提醒他,弟弟背着他而他吊在一个绳子上,在警察来的时候弟弟拼命的吹口哨,但是哥哥不幸的挂在了绳子上而弟弟没有支撑住他,哥哥吊死了,弟弟于是疯了他疯狂的吹口哨,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都管他叫口哨人。在这个故事里,弟弟免于死亡的最后的方式便是无止境的重复那个令他痛苦的过程,不断的寻找那个他已经失去的不可能的存在。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不断在其他的galgame中寻找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对象a。
这便是圣兆,它不再像症状一样需要解读,它只是在无意识的积累关于享乐的能指,同时维持波罗米结环的运转,或者说它就是被完成的症状,就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佩内诺普织布一样,织了又拆,拆了又织仿佛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因为这就像加缪所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因为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与最后的爱。

五.结语
这是我们物种的无法避免的悲剧因为:“我们物种不能以自己本身度过自己一生的悲剧,在主体构成自己原型的那个原始的地方就已经注定。”
我在最后只想说的只有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在《路边野餐》中主角在最后见到那个能实现他愿望的魔球时他说的话,他本想实现让他女儿好起来的愿望,但这时他这时什么都说不,他只能不断的重复说出哪句话:“每个人都幸福快乐,自由,愿世人都能得到幸福。“
希望每个人都快乐幸福,愿每个人都不会一次次的重复我们那个原初创伤的悲剧。

本文转载自B站 cv8463462 已获得原作者 dieholmes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