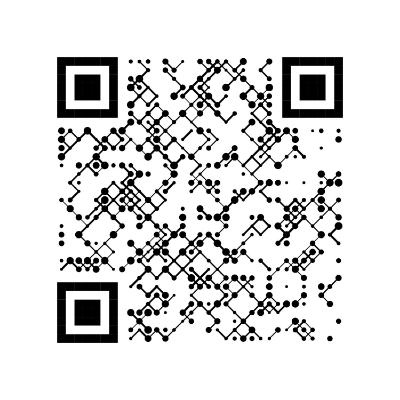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大姐姐?
加缪说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对我来说,我也必须想象这些女孩子们都是大姐姐。
在白色相簿动画中,藤井冬弥将周围的女孩子都称作女神,因冬弥曾经目睹青梅竹马遥被欺负却无力保护,这一事件成为他内心的创伤。成年后,这段记忆被压抑,但通过松山玛瑙的介入得以重现。玛瑙曾在小冬弥最无助时出现,教会他通过“将女性视为女神”来逃避现实痛苦,认为这种方式能避免伤害自己和他人。 玛瑙的引导使冬弥形成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将女性神圣化,他得以从现实的情感责任中抽离,同时缓解因自身软弱产生的愧疚感。
藤井冬弥通过对女性的神圣化消解自己的情感责任缓解自己优柔寡断的伤痛,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想象每个同龄女孩都是大姐姐 使自己的主体性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 暂且忘记自由与责任的恶心 才能令人感到片刻的安息。
萨特的存在主义命题“存在先于本质”是其所谓“恶心”的关键。人类没有预设的本质或意义,必须通过自由选择创造自身价值。但这一自由也带来了沉重的责任和焦虑:当人意识到自己是绝对自由的(没有上帝、命运或本质的束缚),同时也必须为所有选择负责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一般“眩晕”。恶心正是对这种自由和无根基状态的直观反应。它揭示了世界的荒诞和人类处境的孤独。
萨特所谓的恶心是一种自由产生的恶心 这比加缪所谓的荒诞更令人感到恐慌。当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时刻 就无可避免的需要承担选择的责任 这种责任带来的痛苦和恶心比西西弗斯看见巨石从山顶滚落那一刻意识到的荒诞性来得更为震撼
我总会想象身边的女孩子们都是大姐姐,因为这样才能使我感到我还是一个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孩子,大姐姐总是有一种母性的美好 母性是最初的 也是最神圣的事物 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也难怪波德莱尔能写出那句“情人中的情人 母亲中的母亲 ”。将女性神圣化为"大姐姐或母亲",本质上是将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状态投射到具体对象上。通过把情感对象抬升至超越性的位置,主体得以免除萨特所言"被迫自由"的焦虑——当他人被凝固为永恒的理想型,主体就不必面对真实关系中动态的"注视"与责任。这种策略与克尔凯郭尔描述的"审美阶段"生存方式存在共鸣,用诗意想象代替伦理抉择,将存在困境美学化。
将同龄的女孩子们想象成大姐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父权的主动瓦解。父权主导语境下形成的男性形象实际是一种压抑情感,反本能的形象。 当父权消散之刻, 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纯粹的孩子。
成为孩子,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之中。许多人都会学着大人的模样说上一些漂亮话 ,装出一副成熟的样子。以为这样就能逐渐变成大人。 但是就像披头士那句歌词唱的For well you know that it's a fool who plays it cool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实际上,这种行为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孤立和冷淡,反而失去了真正的情感交流和温暖。其实真正的成长是像王小波说的那样—— 一个人是在一个漫长的遭受捶打的过程中渐渐成为大人的。
galgame中常见的姐姐系角色 正是这样一种神圣的存在,无论情况如何糟糕,无论明天是否是世界末日,只要有有大姐姐们在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