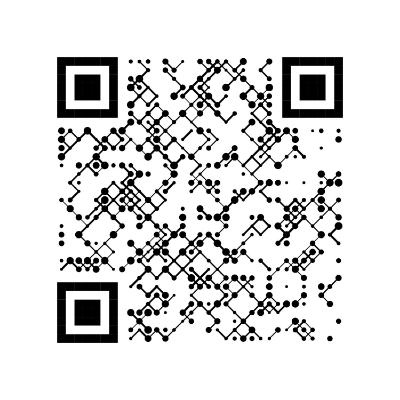浅谈《天津罪》:试论Galgame的剧情结构

(水无月萤镇楼)
一个幽灵,一个“kanon问题”的幽灵,在Galgame的上空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美少女游戏界的一切势力,高桥龙也与麻枝准、奈须蘑菇与虚渊玄、讲谈社的《浮士德》编辑部与早稻田的文学教授们,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单线叙事的剧本家不被它的竞争者骂为“剧情锁的奴隶”呢?又有哪一个试图全选的玩家不被指责为破坏了“纯爱”的更激进的元小说暴徒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救济的排他性已经被公认为一种难以回避的游戏本体论力量。
现在是剧本家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解法、自己的True End倾向,并拿“光玉”、轮回与“Meta视点”来反驳这个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以上为Gemini所写(笑)
简单来说,以Key社的第一部成名作kanon命名的所谓“kanon问题”,即“救济的排他性”问题,是指世界系Galgame在剧情结构上的根本矛盾:为了达成某个女主的HE,男主必须“进线”并投入全部的时间和资源,这种“救济”是排他的、不共可能的,因为男主在其中的存在与参与本身就是不同可能世界中最大的变量。这种排他性在共通线-个人线的树状结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玩家选择走进A线,B线和C线女主就会因男主的“不在场”而陷入悲剧。

(想想柚子社的流程图)
对绝大多数废萌作品来说,这个问题是在甜甜的日常中被无视的:玩家可以在共通线积累好感度,进入对应的个人线与女主展开甜甜的恋爱,也可以深入女主的个人历史,在矛盾和危机的化解中收获自我与彼此的成长。甚至于,玩家还能饶有兴致地在其他个人线中“观赏”心仪女主的败犬模样。

(没错,我又来迫害Nanami了)
言归正传。对“救济的排他性”的第一种解法是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战”。首先,我们承认每一“平行世界”的独立和平等,承认每一条个人线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然后,通过剧情锁,在“遍历”每一条个人线后,设定一个“真结局”来拯救所有人。2003年的Clannad之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作品,与其独特的“光玉设定”对排他性问题的解答是分不开的。在这里,问题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平行线,不再是“为了拯救真女主,是否必须牺牲其他人的幸福”,而变成了“只有当你先在这个宇宙的所有可能性中拯救了所有人,你才有资格在最终的奇迹中拯救真女主(渚)。”未被选择的平行世界的幸福,在被记录的存档中内化为玩家真实的体验,并在最后获得了完成的那个总体性的救赎面前保留了其意义。

(banana作图)
对“救济的排他性”的第二种解法是所谓的“Meta视点”。同样依赖于共通线-个人线之后的剧情锁和“真结局”,“Meta视点”放弃了“小镇的奇迹”,不相信男主在剧情内部能够拥有拯救所有人的力量。排他性无法在平行世界之内得到真正的解决,因而“打破第四堵墙”就成为了最后的出路。玩家作为“观测者”不同于游戏主人公,拥有更加高维的视点,正是此一视点之差让“突围”成为了可能。在《Ever17》中,只有处于高维视角的“Blick Winkel”才能观测到所有平行世界的信息,从而解开谜题。而在《寒蝉》中,梨花经历了千百次轮回,玩家的每一次Game Over都是通往解的积累。这里,“排他性”变成了“试错法”。
对“救济的排他性”的第三种解法是存在主义的“决断”:幽灵无法被战胜,也不必被战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它,直面它。这里,最为典型的是奈须蘑菇(Nasu Kinoko)对Fate/stay night的评论:在这个上帝已死、一切宏大叙事都宣告解体的后现代社会中,个人没有能力、也无需为整个世界负责。HF线的士郎通过“只做樱一个人的正义伙伴”,以一种放弃普遍救赎理想的方式寻求一种存在主义的个体性的解决。

(这两段小资历其实了解得都不太深,所以只能简述了)
当然,还有一种解法是宅宅们喜闻乐见的后宫结局。然而,“后宫”究竟是解决了问题,还是回避了问题?这可能才是更值得玩家们去深思的地方。

(丛雨大人有说法)
我们今天要谈的被誉为紫社巅峰的《天津罪》,与以上几种解法都不同。在笔者看来,《天津罪》并没有“解决”排他性的根本矛盾,而是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深化了这个问题。
首先,“救济的排他性”的前提是什么?是在我们前文所述世界系Galgame中共通线-个人线分叉式的剧情结构。无论是剧情锁还是AfterStory,都无非是在这个基本的“平行世界”的框架内打的一个补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抛弃掉这个剧情结构?进入《天津罪》的玩家很容易发现,这里的形式结构并不是传统Galgame中树状的,而毋宁是鱼骨状的:共通线结束后并没有交给玩家自由选择个人线的空间,而是依次进入心、响子、爱和萤四个人的个人线前期剧情。亦即,作者实际上把个人线剧情一分两半:每一章个人线的1-8节(记作Part A)放在主线剧情中,9-12节(记作Part B)则分叉出去作为个人线End。即使是最后登场的真女主萤,无非是通过剧情锁隐含了一个TE,只看NE无疑也遵循这一结构安排。

在传统的世界系Galgame中,各条人物线平行发展,在理论上归属于“同一个时间点的不同世界线”。在这里,游戏主人公排他性地只能身处其中一个平行世界之中,故而必须求助于某个遍历所有世界线的Meta视点(无论这个视点来自世界之内超个体的“小镇”还是世界之外的“玩家”)。而在《天津罪》中,这个问题被转化为了“同一个世界线中的不同时间点”,世界之间的排他性被转化为了同一世界之中的时间顺序问题。这当然并非是对排他性问题彻底的回答,但这种转化恰恰揭示了被原先的世界系问题所掩盖的读者时间性维度:游戏内时间的形式平等性永远无法取代玩家游戏体验的时间不平等。
在世界系Galgame中,“平行世界”之间不存在时间性维度的差异,或者说作者费尽心力试图抹杀掉这种时间性差异以尊重每位女主的独立性和彼此的平等。每一次点击New Game重新进入游戏,玩家与剧本家之间相当于签订了一个虚拟的契约,它要求我们“忘记”前一段剧情体验,以一种全新的或者说“失忆者”的姿态重新进入下一段剧情。

然而,我们总是先推一个角色线,再推另一个角色线,“失忆”的契约从来就不存在,毋宁说玩家线性的时间体验决定了女主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完全彻底的平等,世界系Galgame向我们许诺的女主之间的平等或许从来就不存在。更不用说,当作者通过锁线或周目的种种形式来为“真女主”铺路或“蓄势”(如《缘之空》中穹妹不能在一周目被攻略,而柚子社则反过来将次要女主锁线在二周目),对玩家自由选择权的剥夺恐怕早就发生了。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拿掉萤线的TE,只看4章个人线,形式上严格的先后之分并不妨碍个人线剧情彼此之间的相互独立。换言之,《天津罪》的篇章结构,与世界系Galgame的“平行世界”不过一线之隔。在这个意义上,《天津罪》的结构反而是最诚实的:剧本家通过对玩家攻略顺序的自由选择权的完全褫夺(在鱼骨状的线路图中,玩家只有拒绝的权利),来将隐含在世界系剧情结构内部的矛盾(平行世界的时间平等vs玩家游戏体验的时间不平等)爆破了出来。
另一方面,“鱼骨图”毕竟只是《天津罪》的形式结构,如果我们深入到剧情之中,我们恐怕还可以提炼出另一个不同的剧情结构示意图。
(以下涉及剧透)

我们来考察一下《天津罪》鱼骨主线中4章个人线Part A之间的联系。如前所述,形式上严格的先后顺序并不妨碍剧情内容上的相互独立,除了心线更具体地交代了共通线未尽说明的言灵之力的局限性,顺序在后的篇章基本并不依赖于此前的剧情。然而,仅仅“独立性”是无法说明剧情内容之间的联系的,因为人物的剧情线终究是同一游戏内的不同人物线。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Galgame中不同角色线之间的联系分为“发散型”和“向心型”两类:“发散型”Galgame强调同一世界观(形式)框架下不同主题(内容)的自由探索,典型如《夏日口袋》,同一个暑假可以有多少不同的展开方式;而“向心型”Galgame强调同一主题(内容)关键词的不同(形式)变奏,如《Clannad》不断反复的家庭主题。而《天津罪》显然属于后者:玩家很容易在后面的人物线中发现之前剧情内容的“既视感”。那么,《天津罪》变奏的主题是什么呢?

当然是“天津罪”啦——不是开玩笑,这个回答是有信息量的。在游戏文本中,“天津罪”只在萤线的Normal End中出现,所谓“夺走一个人拼尽一切想要活下去的意志和愿望,即使是全能的神所为,也是罪恶”。然而,所谓“天津罪”仅仅说的是萤线NE的剧情吗?虽然并非不可,但这种解读显然削弱了其他几条人物线在剧情结构上的作用。笔者的倾向是,我们需要对这个主题进行适当的“放大”,在一个更加广义的含义中去统摄整个游戏剧情。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剧情:4个Part A让我们体验到的“既视感”到底是什么?在织部心篇中,男主诚试图用言灵之力拯救癌症晚期的杏月,并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最后在爱的帮助下实现了阶段性的大团圆结局。而诚也意识到了,当初驱使自己走出村子的那个“去吧”(行きなさい)实际上是“活下去”(生きなさい,音同iknasai),是母亲对自己最后的祝福。幼年时诚的母亲用自己的性命来交换了诚的性命,而现在诚又试图用自己的性命来交换杏月这位“母亲”的性命。在这里,剧情设计为诚因为自己的“功力”有限而未能实现“换命”,并没有让诚去严肃反省其中的对错。

在接下来的朝比奈响子篇中,主角变成了响子和她童年的挚友铃夏。童年时期在湖边戏水时,响子因为某些意外落入水中,但最后去世的却是救她的铃夏。在诚的怀中哭诉背负这一切走到今天的响子突然发现,那个梦魂中的铃夏又出现在了她的眼前,并且还在每日不断地成长。与之相对,响子的身体却不断地消瘦下去:原来,铃夏的生命力全来自于响子的让渡。在这里,打破“换命”逻辑的并非“人死不能复生”,而是这个被响子复活的“铃夏”并非“真正的”铃夏,而只是存在于响子心中的理念,是在响子不断地“追忆”中被“询唤”和塑造出来的形象。而已死之人的理念之所以被询唤出来,其目的也是为了生者的“心安”,为了能够让生者与死者做一次真正的告别。

在笔者的游戏体验中,紧接着响子篇的恋冢爱篇具有最明显的“既视感”。随着剧情推进,我们发现,幼年时在村子里,最初与诚谈婚论嫁的并不是恋冢爱,而是她的姐姐恋冢希(果然Galgame男主的失忆症是标配hhh)。爱出于某种当时尚不自觉的嫉妒,无意中使用了言灵之力,让出村采购的希染上了传染病,不仅带走了希的性命,也差点带走了诚,并算是间接害死了诚的父母。爱对诚的感情从而远不只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两个人之间的青梅也好婚约者也罢,而是还带着希的感情和意志,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爱的灵魂,化作那一场夏日雪的诅咒。临死的希的确对爱有所托付,但雪的诅咒却是爱强加给自己的,因而虽然剧情中是通过诚召唤出了希的“言灵”来一场姐妹的再会,但最终也只有爱自己能解开自己心灵的魔咒。这就是第三幕带给我们的启示:没有人需要代替别人而活,也永远不必成为另一个人的“影子”或者“替身”。

不难发现,在《天津罪》主线剧情的前三章(个人线Part A),三个故事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剧情支点:“以命换命”。人既不能代替另一个人去死(响子线),也不能代替另一个人去活(爱线),毋宁说“以命换命”这件事本身就是被禁止的(心线)所谓“天津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神的面前,每个人的生命是等价的,这是1=1的逻辑铁律。但对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和对方都是一样的人,没有权利代替对方做出生与死的决断。而作者在这里更加激进地试图表明:即使是有能力予取予夺的神,违抗人的意志而行性命之间的“等价交换”,也是一种“罪”——“天津罪”直译即“神明所犯的罪”。围绕此一“天津罪”的母题,作者带我们分别从“亲情”(心线)、“友情”(响子线)和“爱情”(爱线)三个不同的“剧场”或“和弦”,来“变奏”和演绎“天津罪”这一主题的不同形式。我想,这才是剧情之间“既视感”的核心。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再来看第四章水无月萤的NE. 作为直接点题的章节,萤线的NE同样涉及到了“以命换命”,而且以一种最为直接、最为彻底和最为残酷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NE可谓前三章的“变奏”所汇聚起来的高峰。然而,我看到网友们大多是将萤线与前三章分开来单独讨论的,这也就意味着萤线也存在其较为明显的独特性。问题也很简单:和谁“以命换命”?在前三章,换命的对象都是一个“他者”,即便是至亲之人,“天津罪”是无论亲情、友情或爱情都不可以逾越的。而萤线这里呢?“自我”难道不正是我们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他者”吗?当曾经活泼开朗的萤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病房,黑萤的模样让白萤都差点认不出自己了。然而,这就足以成为剥夺黑萤的求生意志,来换取白萤生存的充足理由吗?这便是NE所揭示的“天津罪”——每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因为人性的光明与幽暗、渺小与崇高共同构成了人之异于禽兽的那个“几希”。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没有成为拿破仑,他疯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而《天津罪》则告诉我们,即使是拿破仑,即使是神,也有属于祂的“天津罪”。
明乎此,TE的结论是顺理成章的:黑萤和白萤本就是同一个萤,因为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渺小与崇高本就相辅相成,不可区分。作为合题的TE必然要超越“以命换命”的“天津罪”逻辑,而指向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融合:当诚让“水无月萤的心合而为一”的时候,我想,这里既可以理解为黑萤和最后一个白萤的融合,也可以理解为黑萤与之前所有白萤的融合——因为在剧情中,最后一个白萤已然继承了前面所有白萤的意志。

回到我们关于剧情结构的讨论。鱼骨图作为《天津罪》的形式结构本身并没有问题,需要补充的是每一章节的内容及其与总体的联系,以及这根作为主线的“鱼骨”本身意味着什么。位于主线的4章个人线的PartA有如以“天津罪”为主题的四重变奏,形成一个盘旋而上的螺旋;而4个女主End(包括萤线的NE)有如螺旋中停止向上盘旋、就该层所探讨的主题(亲情、友情、爱情与“自我”)从螺旋中飞出的切线。而最后的TE,则是收束了整个螺旋的黑格尔主义的融合。

那么,那根鱼骨,或者说螺旋的轴线是什么?显然,我们有必要将视角从单一主题视角内的女主转移到推土机般推倒所有人的男主。男主是神的后裔,是从与世隔绝的村子中走出的“言灵之神”。而在故事的结局(TE),男主失去了神力,彻底成为了人。很明显,当我们将故事的开头结尾连起来看,《天津罪》讲的就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天津罪”则是具体的学习“途径”。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天津罪》的精神内核其实是所谓的“教养小说”(Bildungsroman)。“教养小说”在中国一般被翻译为“成长小说”,如现当代文学史“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中的《青春之歌》,其核心内涵可追溯到1795 年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德语词Bildung的词根是Bild(图像),强调心灵的陶冶和塑造,所谓“教养小说”,讲的正是主人公通过外界的漫游,最终习得更加圆融和坚强的内在心灵的过程。将这层意思放回到我们的《天津罪》中,我们就能更加明显地看出,整部《天津罪》无非就是主人公从神到人的学习过程,是褪去神力,习得人性的成长过程。无论是围绕“天津罪”所展开的亲情、友情、爱情还是“自我”的探讨,最终都是要我们的主人公放下神的傲慢,去理解和接受每一个生命的独特价值。

我们讨论到什么地方了?能看到这里的读者真了不起。我们从世界系Galgame的内在矛盾,即“救济的排他性”或者说所谓“kanon”问题讲起,讲到了《天津罪》的线性结构抓住了被世界系Galgame否弃的读者时间性维度,最后发现《天津罪》讲的居然是一个传统的教养小说的故事。喂喂,Galgame作为Game而不是novel,不正在于其相较于传统小说所打开的更加丰富多元的可能性空间吗?这岂不是在说,《天津罪》形式上的“反叛”,本质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吗?我们恐怕不能这么说,倒是要反过来,《天津罪》是用世界系Galgame的结构形式,来改造了传统的教养小说,因为教养小说最多只能是主叙事线,《天津罪》还包含了鱼骨的分叉或者说螺旋的切线,这些分叉出去的世界线End本身已经超越了教养小说的单一结局。毋宁说,《天津罪》的这一“嫁接”乃至“复古”,是要我们去反思传统Galgame以进步为名的“平等的平行世界论”:当作者向玩家们宣称和担保每一条个人线形式上的平等的时候,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X号位女主”的内部的次序排列吗?而当玩家带着上一个女主的记忆去攻略下一个女主的时候,New Game“遗忘的契约”又有多少真实的分量?同样想要让玩家放在末置位攻略,与其无视这个幽灵,羞羞答答地通过剧情锁埋一个真女主,不如通过对玩家选择权的褫夺来明明白白将作者想要塑造的那个最终的真女主烘托出来。我想,这可能才是《天津罪》想要传达的叙事“野心”,也是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剧情结构的杂谈本该到此为止,但最后我还是想借此来简单地聊一聊剧情本身。(
我知道我已经讲得够多了所以
)我们就单单来看水无月萤的这句话:

刚刚推到这里的时候,这句话带给我的不是感动而是扎心:为什么每一个重生的水无月萤都会义无反顾地爱上男主诚?因为男主在这里成为了每七天重生的白萤得以维持其自我同一性的锚点:直到遇见男主,白萤的自称才从“萤”变成了“我”;直到遇见男主,白萤才拥有了其不同于黑萤的独立的自我意志。因而,某种意义上,不是“无论重生多少次,我都会爱上你”,而是“无论重生多少次,是你让我成为了“我””。
但转念一想,即便如此又如何呢?白萤的七天轮回不是为了打破什么,而是她存在的前提,她必须接受这个轮回,并在其中起舞。这是一种古典的对命运的承担(Amor Fati / 爱命运),作为尼采意义上“积极的虚无主义”,她将这个来自命运的诅咒转化为了自愿的誓言:即便知道结局是消亡,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替代品,她依然在每一个七天里全情投入地去爱、去感受夏天的天空。我想,这才是我们高中背过的那句尼采名言的真正含义:“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