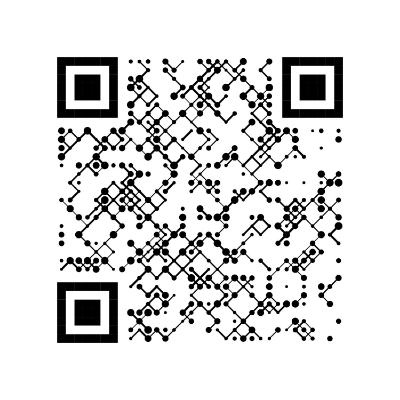“家族”是如何“发生”的? ——重读田中罗密欧的《家族计划》
2001年,日本著名剧本家田中罗密欧发行了他的第三部作品《家族计划》。古往今来,以“家族”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但被这个标题吸引而来的玩家很快感到了“背叛”:田中根本所写的根本不是一般读者所设想的传统意义上的血亲家族,而是七个现代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原子个体“报团取暖”所形成的“拟似家族”。尽管发行时销量不佳,《家族计划》却长期被奉为神作,在日本的权威评分网站“批评空间”中长期保持了90分以上的超高分。在笔者看来,除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怀、巧妙的剧情设计和极富时代气息的“电波系”的文风,只看作品对“家”与“家族”本身的存在论的叩问,对二十多年后今日的中国读者而言,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剧透预警
*私货拉满预警
引论:作为“思想实验”的“家族计划”
故事的剧情始于在中餐馆打工、独自生活的男主角司偶然“捡到”并收留了一名来自中国丽江、只身前往日本寻找生身母亲的偷渡客春花,随后被黑帮威胁失去了住所。之后,主角又先后结识了破产的原企业家宽,自杀未遂的被骗婚少妇真纯,以及离家出走的女孩茉莉。他们“借住”在停水断电的“空宅”高屋敷家,并在从事地下生意的前合作伙伴准的帮助下与继承祖宅的名义房主、落魄画家青叶形成了“家族计划”的契约,对外统一使用房主“高屋敷”的姓氏。

表面上,“家族计划”作为这些边缘(底层)群体的“社会契约”,直接来自于“分担房租和生活开销”的经济需求。但田中并没有为笔下的人物安排一个适合“报团取暖”的寒冬;相反,在故事所发生的夏天,“家人”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亲近到“报团取暖”的程度:春花只想着和司玩;真纯动不动想自杀;青叶独占唯一拥有空调的房间,对谁都爱答不理;准则保持“生意伙伴”的冷漠,在一家人的饭桌上也只吃自己的压缩饼干。“家族计划”的发起人宽作为剧本中的搞笑担当,完全没有父亲的严肃,而被动加入的男主则清醒地保持着界限,和读者一起始终在反思那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人是可以一个人活下去的吗?
在笔者看来,整部《家族计划》可以看做是田中的一场“思想实验”——他“悬置”了家族天然的生物学属性(血缘),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回到事情本身”,将一群完全异质的陌生人抛入一个共同的空间,以此去观察“家族”这一存在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发生”(Ereignis)的。
一、回不去的“原乡”:作为悖论的原生家庭
什么叫“家族”的“发生”?由父母长辈所组成的、每个人都拥有的原生家族,难道不是先在于个体的、是我们生来就被决定的吗?的确,从儒学传统的视域出发,人并不是生来“被抛”的;即使在出生前,我们就已经“存在”了:他存在于父母长辈的期望和想象中,存在于那个尚停留于能指符号的“姓名”中,存在于“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伦理链条中。当我们第一次用姓名来自我指称,父母的期许与自我的意志形成了真正的“视域融合”。

然而,为什么愚公的子孙就必须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祖辈的意志,而不能有自己的决断?就连孔子也只是要求我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年之后就可以开启自己的人生。更进一步说,为什么所有这些先在地加诸于个体的家族的意志就必须无条件地被个体所接纳?亦即,为什么他(她)能成为我的家人,就因为我的身体中流淌着他(她)的血脉?在“家族”的生物学与存在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被抹去的巨大的鸿沟;而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直面和解决的时候了。
在《家族计划》中,“原生家庭”表现出一种悖论的性质:它既是创伤的来源,又是人们无时不希图复返的原乡。一方面,“家族计划”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各自舔舐伤口”的互助计划:司和茉莉都被原生家庭所抛弃,被寄养家庭百般折磨和虐待;春花是其日本母亲在中国留学期间被轮奸的产物;青叶被自己的原生家庭当做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家族企业间“和亲”的工具;准更是被父亲性施暴,被母亲虐待,为保护妹妹独自喝下母亲为她们准备的毒药,从此不但不吃除压缩饼干以外的一切食物,还与唯一的妹妹产生了深深的误解。或许有些读者会就此感到暗黑,但笔者所想到的却是身边或是新闻中报道的真实案例。笔者在这里无意对中日两国的历史与现实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只是想起了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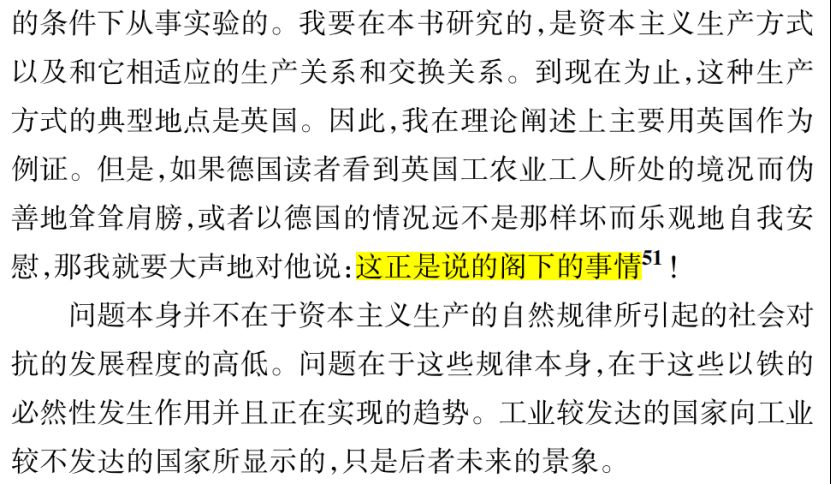
(插嘴:最近很火的“斩杀线”同理)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田中会赞同所谓“父母皆祸害”,认为真正温暖的家庭只在完全舍弃血缘关系的“家族计划”中才有可能存在呢?也不尽然。几乎在每一条人物线,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与原生家庭的“和解”。司最终发现,其被原生父母“抛弃”的真实原因是一场意外的车祸,是母亲用身体保护了年幼的主人公;春花的母亲如今已经有了自己新的家庭,且对过去在中国的经历仍怀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作者最终仍让女儿为不能相认的母亲及其家人准备了一桌亲手做的晚饭。
青叶线中,田中更是利用一只小小的竹蜻蜓巧妙设计了双重的反转:在第一重反转中,青叶根据童年日记中的回忆,拼命发掘那承载了与爷爷过往温情岁月的竹蜻蜓,但青叶不愿面对却被主人公揭穿的事实却是,就连日记本身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青叶的祖父作为她“逃婚”出来后唯一接纳她的家人,对她也从来没有给予任何的温情,包括青叶再三央求的竹蜻蜓,祖父也从来没有动手将其修好。就在读者恍然大悟,以为撕去了幻想后的原生家庭再无任何温暖可言的时候,本该作为“时光之匣”埋在地下的竹蜻蜓却出现在了祖父上锁的抽屉中。原来祖父之所以独居在高屋敷宅,本身就是家族内斗的结果:作为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却被自己的亲儿子夺权后“放逐”至此。他当然理解青叶作为政治联姻牺牲品的痛苦,但作为一个将死之人,他希望培养青叶的独立和坚强,将冷漠视作是切断依恋、避免给青叶造成二次伤害的唯一的慈悲。拙于表达的爱就像那修不好的竹蜻蜓,连同已成废墟的过往随高屋敷宅在大火中埋葬;祖父留给青叶真正的遗产是另一处乡间的住宅,青叶将在那里开启新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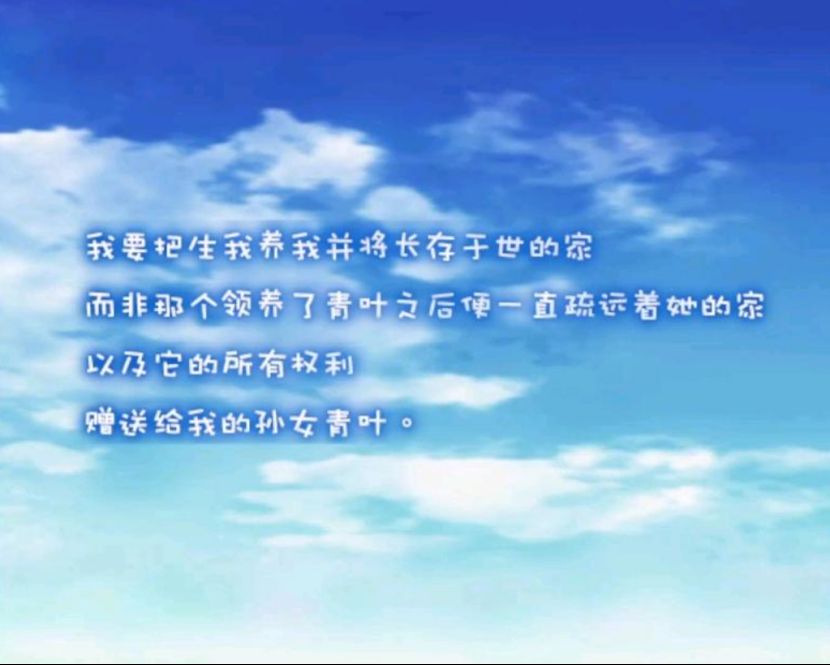
或许,真正的原生家庭就像青叶线中的竹蜻蜓:这里没有绝对的恶,也不存在幻想中的美好,有的只是那个残缺的、不完美的真相。然而,剧情中的人物要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实现最终的和解,对这个“回不去的原乡”行最彻底的“祛魅”,又不得不首先重返废墟现场。在所有人彻底放下对“原乡”的执念之前,“家族计划”在存在论上注定是无根的:既然大家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各自舔舐伤口”,伤好了就要各自“回家”,高屋敷宅就永远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避难所”。七个原生家庭的引力从各个方向撕扯着这个脆弱的“家族计划”,其最终的失败因而有其绝对的必然性。
二、血缘、权力与金钱:否定的辩证法
游戏中,除了主角团的“家族计划”,田中还设计了两个直接的“对照组”,从反面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家族”可能的异化形式。首先是青叶的原生家庭,亦即真正的“高屋敷家族”。青叶被家族当作企业间“政治联姻”的工具,而祖父则在针对他的“玄武门之变”中失去了权力地位,被勒令退休。“家族企业”正是这样一个更加恐怖的怪物,当封建权力关系获得了资本的肉身,封建的家庭伦理与资本逻辑的双重宰制让个体既没有现代社会的自由,又得不到传统家庭的温情。可叹的是,这样的“家族企业”作为双重地狱的叠加,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依然普遍存在着。
(“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鲁迅《拿来主义》)
如果说“高屋敷家族”是“家族计划”的显性对照,那么刘家辉(司打工所在的中餐厅老板)的黑帮“家族帮”则与其形成了另一种更加隐蔽的对照。“家族计划”的故事始于春花被“上 海 帮”拐入日本,继而被“台湾帮”抢走,又趁乱逃脱并在刘家辉的授意下被司所收留。刘家辉试图以此挑拨“上 海 帮”与“台湾帮”的斗争,从而坐收渔利;而在几乎每一条线路中,他都取得了成功。

不同于依靠同乡或宗族关系来保持内部凝聚力的“上 海 帮”和“台湾帮”,“家族帮”的成员来自于世界各地,颇有一种《水浒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神似。不仅如此,刘家辉利用春花将司卷入黑帮仇杀,并在司失去一切的时候试图通过联姻拉他入伙,这种通过剥夺对方的独立性,从而半强迫地建立依赖关系的方法,也与水泊梁山拉拢秦明、卢俊义这些良民或体制内人物的手法如出一辙。不同于“高屋敷家族”将“家族”变成了“企业”,“家族帮”则将“企业”变成了“家族”。当“打工人”和“老板”换位为“小弟”与“大哥”或者“三舅侄儿”与“四姑姥爷”,“家族帮”作为企业化的黑帮,其底层的资本与权力关系就被完全掩盖了起来。
“家族计划”作为一个探讨存在论家族之“发生”的思想实验,作为一次对理想家族试验性质的探索,势必要求对以上两种家族形式行彻底的否定。我们看到,这个由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体所组成的“拟似家庭”模仿了血缘家族的形式,但扬弃了附加在父母子女关系上的封建人身依附与权力支配关系;它和“家族帮”一样由陌生人组成,又守护着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没有“以家族的名义”吞噬个体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个稍显拥挤的宅院中,田中还通过屋顶的夜空,为主角们保留了一方畅谈过去与未来的私密空间。

然而,“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的问题有如悬在“家族计划”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即便在最空想的“家”的乌托邦中都必须妥善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从故事内部的逻辑来看,“家族计划”始于“分担房租”的经济需求,终于黑帮威胁下无法克服的经济困境,自始至终根植于经济理性的决策。笔者不禁想起一百年前,鲁迅在北京女子高师讲《娜拉走后怎样》,为当时刚刚走出“四世同堂”封建大家庭的学生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斩断旧家庭的羁绊是有条件的,没有的物质基础的“独立”只是镜花水月。田中显然并不否认鲁迅的命题,故事中的人物们确也长时间挣扎在“堕落与回来”之间;但田中又比鲁迅往前又走了一步:有了钱,有了出走的路费,娜拉的问题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了吗?

《家族计划》发售于2001年底,其时主打“泣系”(催泪)风格的Key社凭借《Kanon》、《Air》等优秀作品风头正盛,田中的《家族计划》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在此类多线路、多结局的Galgame中,当玩家选择“攻略”某一位女角色,其他未被选择的角色就有可能在该剧情线中遭遇不幸。此即“救济的排他性问题”,因1999年发行的《Kanon》又被批评界简称为“Kanon问题”。

而在《家族计划》中,田中同样安排了一个类似的排他性问题:代表玩家的男主角司得到了真纯的信任,可以自由支配真纯母亲留给她的30万日元的遗产。好巧不巧,游戏中解决每个人危机的“价码”正是30万日元:这笔钱可以还清宽所欠下的经营贷款;可以帮春花从黑帮那儿赎身;可以帮准拯救濒临倒闭的孤儿院;也可以交给茉莉的养父母或真纯的婚约者来解除痛苦的家庭关系。
看起来,这笔钱只能用来救一个人;在游戏的不同个人线中,主角也都做了自己的选择。然而,问题没有一个因30万日元就得到了解决——我们看到,当司还清了债务,回到自己真正的妻女身边,原先因躲债而“战术性离婚”的妻女已经不认他这个丈夫和父亲了;30万日元或许能买通黑帮的头目,却买不通国境线和法律所代表的国家暴力机器的绝对力量,春花到底还是被引渡回了中国;准为了从小与妹妹一同生活的孤儿院不惜出卖身体、贩卖黑帮药物筹钱,但在那个大萧条的年代,个人的小额资本注定无法填补社会福利体系崩塌的黑洞,孤儿院的倒闭绝非一人可以改变的;30万日元固然可以从茉莉的养父母手中买断抚养权或切断真纯与婚约者的羁绊,却也不能就此担保由柴米油盐所奠基的新生活的幸福。在高度现实主义的田中这里,没有麻枝准笔下的奇迹,也根本不可能用钱来买到这样的奇迹。

一言以蔽之,30万日元不是面向未来的“安家费”,而是面向过去的“分手费”,是用来与旧家庭、旧生活和旧时代做最彻底的切割和清算的“赎金”。如前所述,“家族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中的每个成员与原生家庭之间剪不断的羁绊;而只有获得了这笔钱,娜拉才能真正毫无顾忌和留恋地摔门而出,用一种决绝的行动,宣布“过去”不再拥有对“现在”的债权,才能拿到“新家”所要求的独立人格的入场券。
三、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论家族的“发生”
什么是“家族计划”?一个分担房租、以“家族”之名共同生活的契约。在游戏中,主人公司几乎是被情感绑架着加入了这个“家族计划”的契约,随之而来的就是持续不断地自我追问:“人是可以一个人活下去的吗?”司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的,他从来没有感觉自己需要一个“家族”的陪伴。事实上,除了最小的茉莉竭尽全力维系着这个“家”,其他人在初期都或多或少自外于这个陌生人组成的“拟似家族”。用德国哲学的语言,“家族”发生了,尽管还处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人们是凭着自己的意志自决加入的这个“家族”,不如说成为家族的一员本身就是“被抛”的结果。田中毋宁在提醒我们:即便我们没有人能够去选择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即便我们生来就必然生活在某个家族之中,“生而在家”的客观现实也并不能改变“生而被抛”的存在论事实。

“家族”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没人能说得上来。然而,在任何人意识到自己是家中一员之前,“家族”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它发生在每天早上全家一起吃早饭的“我开动了”的仪式中,发生在每天“早上好”“我回来了”“晚安”的问候中,发生在每个夜晚屋顶星空的私密絮语中。它发生在“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吵架和拌嘴中,发生在彼此看不见的牵挂和惦念中,发生在日渐熟习的统一的“高屋敷”姓氏中。

“家族”并不因为登记领证或孩子的出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正如拟似的“高屋敷家族”并不因经济契约的一致通过而自动诞生。家族的“发生”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在过去某一时刻已经完成了的事件,毋宁说,过去的时刻要成为家族的历史性“发生”的起点,它就必须被批判、被超越,像脉搏和心跳那样绵延并“回荡”在当下人们的意识结构中(例如,对结婚纪念日或孩子生日的庆祝)。又或许,根本不存在某个可以被追溯的历史的起源,历史时刻的真实意义只有在失落后的再次追忆中才能被寻回或重新发明。没有人说得清这个拟似的“高屋敷家族”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地“发生了”,但就在宽宣告“家族计划”结束的时刻,就在所有人远远望着被烈火焚毁的高屋敷宅的时刻,过去大家围坐在一起喊“我开动了”的日常才显得格外令人心痛。

对“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发生了”,而是“发生着”:过去如脉搏和心跳般在当下持续地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家族计划”时期的主角团,由于未能彻底割离他们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原生家庭的过去还在不断地“发生”,不断侵噬着“拟似家庭”当下的生活。这是“过去支配现在”:原生家庭的幽灵徘徊在高屋敷宅中,而幽灵是没有未来可言的。而当高屋敷宅被烧毁后,主角团没有选择就此好聚好散,而是凭借过去的回忆,共同存钱去再造一个新的高屋敷宅。这是“现在支配过去”:现在终于可以通过对过去的拯救来真正走向未来。

从前的高屋敷宅只是一个“避难所”,人们被过去的阴影赶入其中寻求一时的逃避。正因其如此,高屋敷宅才必须被烧毁,“家族计划”才必须被终结:真正“自为”的“家族”开始于“家族计划”终结的时刻,开始于主角团通过各自的劳动,共同存钱去再造高屋敷宅的时刻。正如本雅明所说,只有被救赎的人才能完全拥有他们的过去。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30万日元的遗产或从天而降的奇迹,它来自于每一个当下自己双手的劳动。重建的高屋敷宅作为“家族计划”时期共同生活记忆的“纪念碑”,既是对过去最后的完结和告别,也是废墟之上自为新家的真正开启。正如我们在官方续作《家族计划~再开~》所看到的:新的家族并不排斥血缘关系本身,但并不将其视作根本乃至唯一的“家族”纽带,更坚决排斥了以血缘为名的封建权力关系。司成为了“家族帮”的二把手,却并没有按照刘家辉的算计与其妹缔结婚姻关系,而是与刘家辉成为了某种充满戏谑却又肝胆相照的“同志”:他们扯碎了捆缚在“家族帮”之上姻亲关系的外在枷锁,在一种近乎“自由人联合体”的黑道江湖中,重塑了关于义气与羁绊的定义。
结语:废墟上的栖居
“家族”是如何发生的?田中罗密欧用《家族计画》告诉我们:它不发生于出生的那一刻(那是被抛的命运),也不发生于签订契约的那一刻(那是生存的策略)。它发生于我们决定不再被“过去”支配,而是用当下的爱与劳动去救赎过去的每一瞬间。
当高屋敷宅的烈火燃尽了所有虚伪的温情与陈旧的契约,“家族计划”作为一个名词彻底终结了。但也正是在这片一无所有的废墟之上,真正的“栖居”才得以开始。它不再需要“计划”来维系,因为曾经的“拟似”早已化作了众人身体里的脉搏。在这个原子化的时代,只要我们还拥有在废墟上重逢的勇气,拥有为了彼此而在此刻共同“发生”的意志,那么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重新发明名为“家族”的奇迹。

(完)